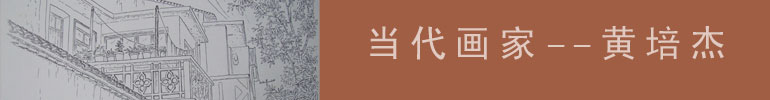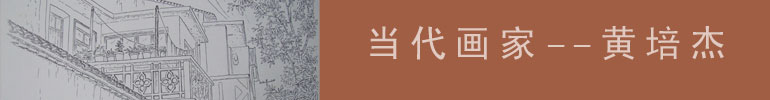三、“光”与“动彩”为内涵的“笔色论”
何为“笔色论”?
如果仅以“笔墨”指代中国画,就无法合理地对唐代工笔仕女画自身的用笔和着色系统乃至其生发的独特审美系统作深入的研究。为使唐代工笔仕女画自身规律得以呈现,把最能体现其特点的用笔、用色方面加以强调,因此形成“笔色论”之概念。例如工笔画的服饰描绘中,我们注意的不仅是表现长袍大袖的程式,而是那套成程式中所蕴含的有独立价值的的东西,即工笔画用笔用色之“笔墨结构”,也就是“笔色”之论,是按笔墨的思维方式派生的概念范畴。
“笔墨”是专指水墨画而言的,具有独立的结构性和程式性,工笔画同样如此。《芥舟学画编》上有“贩夫贩妇皆冰玉者也”之说,即人脸中有笔墨应用的好地方,就连“贩夫贩妇”也能成为笔墨表现的最好对象。这说明着笔墨的独立性和广大的面向性,是从“技”的角度上讲的。“笔色”也应该有如同笔墨相同的独立和面向性,并且,它还具备笔墨所不具备的“色彩性”。“绚烂之极复归于朴”,是较为复杂的哲学观念,“朴”,可以理解为墨色,但更是指色彩的朴实,即自然而然的和谐,这同儒家“和而不同”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画有着一套独特的,并且非常完善的品评标准,并非使用色彩和线条就是中国画,应发掘自己的“真”东西出来进行学科建设。“笔色论”虽是由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研究中提出,但也是在整体中国画的标准之中建立的,这个标准大体是:以“六法论”为指导思想的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画面审美观(气韵生动),造形观(骨法用笔和应物象形),赋色观(随类赋彩),构图观(经营位置)和继承发展观(传移模写)。
|